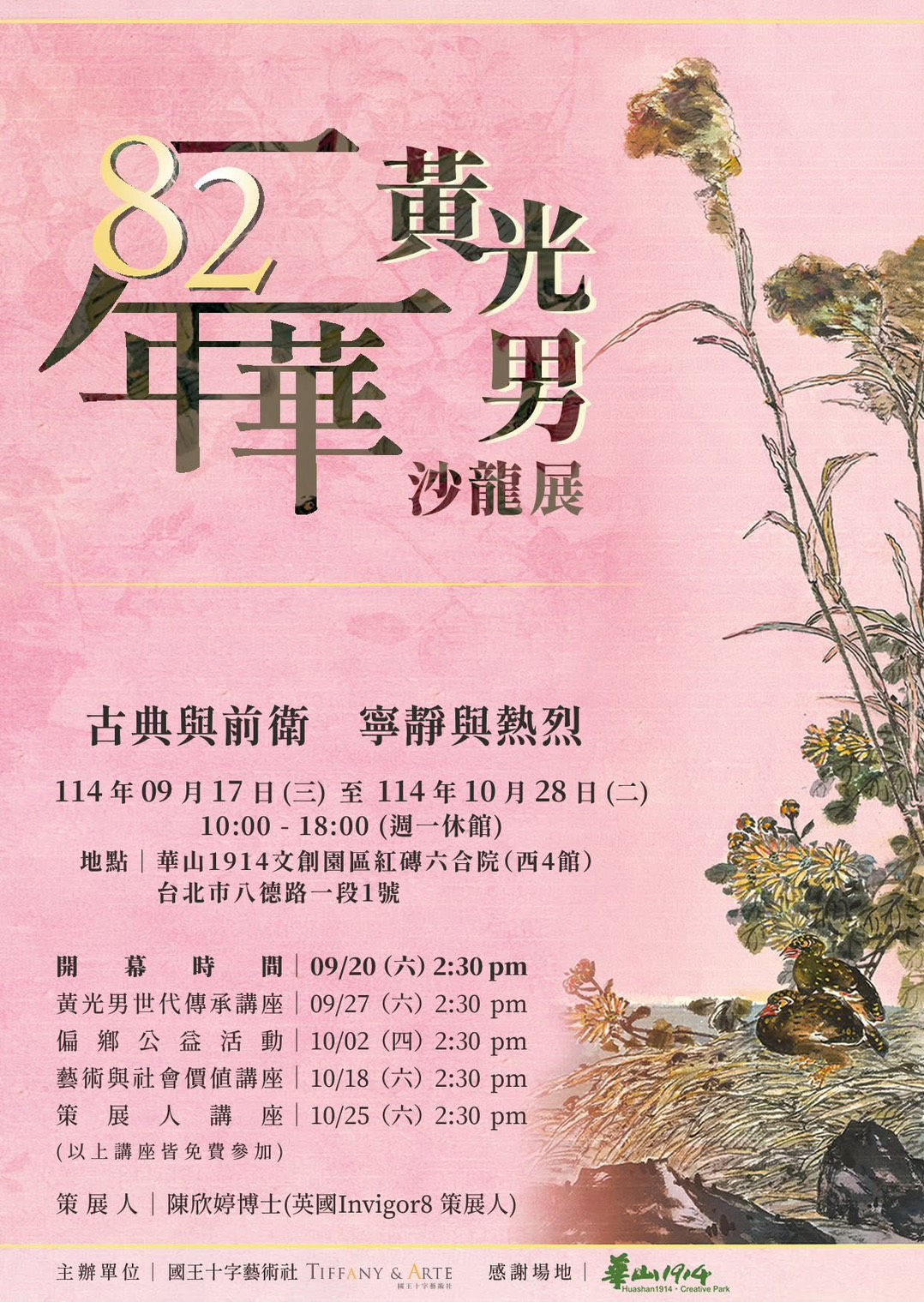文/陳仲祺 台北市影音公會理事長/資深媒體人。
電影《突破‧三千米的泳氣》以看似不可能的真實壯舉為主題:七位視障者橫渡日月潭,把黑暗一寸寸變為閃爍的航道;每場試映會總在掌聲與低語中緩緩落幕,觀眾離場時帶著眼角未乾的淚痕與久久不散的悸動。
導演安景鴻起初打算拍一部安靜而誠懇的紀錄片,然在一次次訪談與陪游中,他發現鏡頭外那種相互扶持的節奏、突如其來的幽默與不滅的信念,比任何旁白都還要有力。原本平實的訓練日誌與反覆的岸上練習,逐漸被他編織成一場關於身體、友情與尊嚴的現代寓言;於是紀錄的忠實被劇情的張力所放大,成就了這部願意把真實擺在光中的電影。

電影以細緻卻克制的筆法還原訓練:淺灘上反覆踏水的節拍、岸邊教練低聲而堅定的指引、游線上彼此的觸碰化為方向的語彙。攝影鏡頭不慌不忙地拉近每一次吸氣與握緊的手,把「看不見」轉譯成聽覺、觸覺與心靈的共同語言。片中既有跨越體能極限的驚險,也有日常裡被忽略的勇氣:晨光下的早餐、夜裡暖燈下的笑聲、挫敗之後再次下水的堅持,這些細節接合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情感能量。
映後,製片人李㼈直言,將真實改編為劇情是一場「尊重與美化之間的拔河」。團隊以當事人口述為根基,以誠意保留關鍵細節,同時在敘事節奏上做出必要剪裁,務求在兩小時片長內把那段長年累月的訓練與情感投資呈現得既完整又動人。片中對日月潭光影的處理,更被觀眾喻為「第三位主角」:水面的薄霧、清晨的粉色光暈、晚霞下抖動的銀線,像是一首為游者書寫的靜默詩章。
試映現場匯聚視障運動倡議者與當事人家屬,掌聲與淚水在影廳彼此回應。有觀眾說,當銀幕上呈現那段並非戲劇化的互助時,才真正理解「看見」可以超越眼睛的範疇。導演安景鴻談及拍片初衷,語氣平靜但堅定:他不欲將痛苦神聖化,而是希望把平凡中的不屈放回眾人視野,讓那些被忽略的勇氣得以被看見。

從更廣的社會觀察來看,《突破三千米的泳氣》超越了單一的運動敘事—它重新挑戰我們對「能力」與「限制」的既有想像。片尾字幕升起時,全場久久未起,沉默中像是一種被喚醒的質疑:在彼此相視的世界裡,我們還能替誰成就不可能?
這不僅是張力與溫度並存的電影文本,也是一場公共對話的起點,邀請觀眾在離開影廳後繼續去看、去傾聽、去參與。